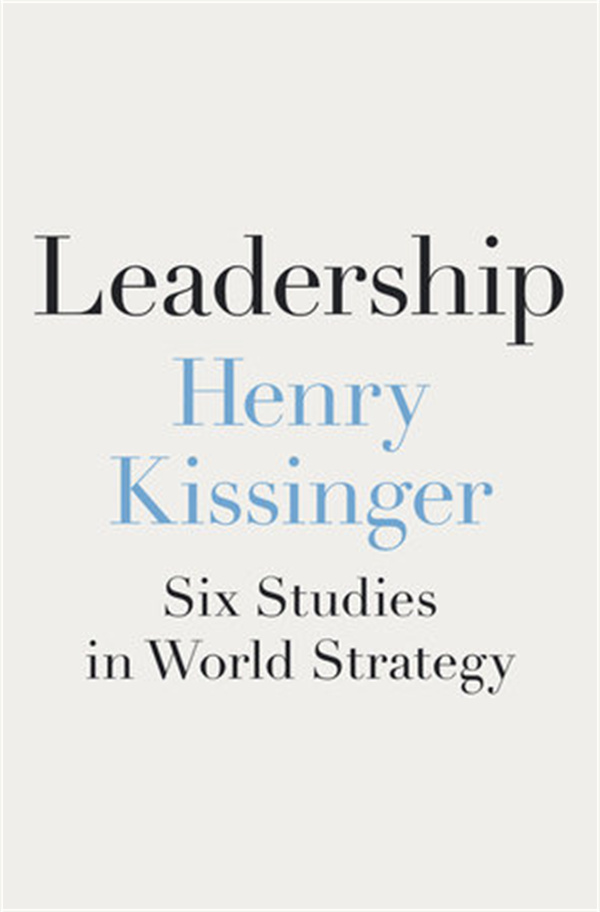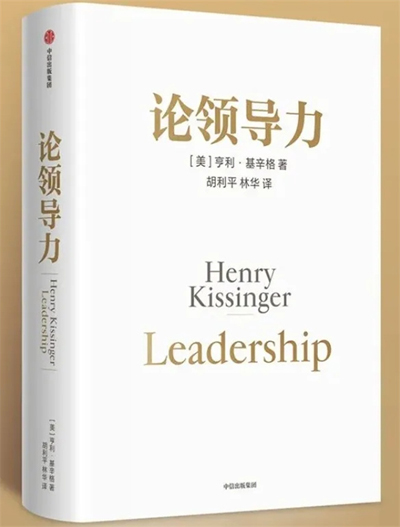王辉耀谈基辛格:现实主义大师最后一部启示录
2024年3月31日作者 | 王辉耀,博士、教授、博导,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理事长
有一位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专家曾提出,对国际关系动向的预测最多只能深达未来十年。这是因为这一动向受到太多变量的影响,很难用具体的模型加以量化。在这些变量当中,至为关键之一是领导力。在整个世界面临错综复杂的挑战和变化之际,领导者的角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历史的走向。
以百年人生观察百年之变局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这一沉甸甸的问题,正是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他的这本著作里想要回答的。
亨利·基辛格
1923.5.27-2023.11.30
在《论中国》《世界秩序》之后,《论领导力》成为基辛格“三论”历史与未来启示录的最后一部。这本书英文版出版于2022年5月,此时新冠疫情已经暴发两年,俄乌冲突爆发三个月,还有半年将会迎来ChatGPT 的公开发布,距离基辛格博士最后一次访华还有一年零两个月,距离他溘然长逝还有一年半。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论领导力》是历史性的,因为这是作者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留下的精神财富。通过百年人生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价值。未来会有很多人,不论是政治家、学者、商人,还是普通的读者,只要他们想要穿透眼前的迷雾,看到未来的走向,就必然会尝试从这位睿智的老人的这部著作中找到理解当下的线索,一如2023年人们试图从他最后一次访华经历中找到未来大国走向的线索。
同时,《论领导力》又是有趣的。它的文本充满着基辛格式的独特风格。基辛格一生著述颇丰。早年的著作如《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学术气息甚浓。随着他从政并经历了若干历史重大转折后,基辛格的著作逐渐形成专属于他的叙事传统。在他的后期著述中,既包括旁征博引的学术理论和观念,也大量掺杂着历史时刻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这样,基辛格的文本往往宏大与细节并重,叙事与评论交织,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当然,这种叙事有时也不乏琐碎。
《论领导力》延续了基辛格后期著作中的风格,但通过改变叙事的对象,其可读性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在本书中,基辛格第一次——可能也是唯一的一次——尝试以简洁的传记方式,刻画六位二战以来与自己有过多次交往,甚至结下深厚友谊的国家领导人,总结了他们的从政经历。通过本书,基辛格告诉读者们,杰出的领导者有若干固有的能力和素质,使之能够穿透社会深层的结构性动荡,影响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
基辛格的不满与焦虑
应该说,基辛格并不打算用英雄史观来证明自己上述观念的正确性。他所选择刻画的六位领导人固然都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意志,但并非都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在他所选择刻画的六位领导人中,萨达特因推动对以色列的和平政策遇刺身亡,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而黯然离任,撒切尔夫人因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至今仍受各方诟病,而阿登纳、戴高乐和李光耀亦不乏争议之处。基辛格有意对这些内容进行了低调处理。他在书中想要突出的是变化的时代背景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二战结束之后,国家政治运行的模式从“贵族统治”转向“精英治理”。这六位在战争之后升起的政治家基本上与传统意义上的治理阶层隔绝。他们大多起步中产,启动政治生涯之际恰逢战前传统的贵族政治被打破,得以进入了上升通道。在他们身上,既存续着此前浓厚的贵族式道德气息,也渗透着中产特有的现实主义行为方式。基辛格想要说明,不论他们的施政成败如何,这些政治家具有的政治品格都是普适性的,是可以延续的。
基辛格用分析能力、战略、勇气和性格几个维度对这六位领导人的领导力进行了分析,似乎想要建立一个分析框架。然而,这只是他做的表面文章。他似乎更在意的是建立一个参照体系,以供读者在未来借鉴。在本书结语当中,他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观念,认为升平日久会导致社会懈怠,从而带来领导力的衰退。对比当下,基辛格认为:“历史上用来评判领导人的标准始终未变:看其能否凭借远见卓识和奉献精神远超自己所处的环境。”
明显可以感受到,基辛格在面对后冷战时期政治人物领导力问题上的不满和焦虑。他暗示了和平年代可能带来的领导力退化问题,总结了领导力应有的特性。从这个角度看,《论领导力》并不是一本对六位领导人进行客观评价的书,而是一本带有作者强烈主观意愿导向的作品。他写的是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六位领导人,但指向的是眼前这个时代。
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基辛格毕生最大的成就之一是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也是眼前这个时代最令他焦虑的大国关系,这反映在他的百余次访华上,甚至在百岁高龄之际、去世之前仍然坚持访华,为两国关系殚精竭虑。两国关系也是各领域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智库(CCG)一直与基辛格保持着联系和交流,并为他与众多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搭建交流桥梁。

2011年6月28日,我参与发起的欧美同学会商会2005委员会邀请基辛格博士参加了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的早餐会,与国内海归精英人士就中美交流、贸易关系、社会多元化发展、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等议题展开交流。

2019年11月21日至22日,我与基辛格博士一同出席了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彭博社共同举办的 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与来自全球的500余位政府官员、企业高管、科技创新者和专家学者等共同商议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探寻当前全球性重要议题的解决方案。基辛格不断重申美中避免公开冲突的重要性,这无疑是非常有价值的。
作为学者和智者,基辛格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性。在去世之前,他与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我曾与后者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共事——联合署名的文章“人工智能军控之路”(The Path to AI Arms Control)警示世人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前所未有、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可怕的威胁,认为全球应在将人工智能全面应用在安全领域之前就制定好限制规则,并敦促美国和中国两个人工智能研发领先者尽快成立工作小组,对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影响进行评估。这篇文章发表在 2023年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之前。同年 11 月 15 日,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之后,外交部长王毅向媒体通报,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机制。
无论是在任公职期间,还是以学者、智者身份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基辛格一向以现实主义大师的身份而为人所知。他自身的政治身份和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政治立场,而他所从事的诸多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外交史的深入理解,使之对现实主义的“均势”与“平衡”推崇备至。《论领导力》一书亦延续了他看待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方法论,那就是领导者的品质、能力和勇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历史发展形成制衡,防止人类文明走向深渊。《论领导力》的创作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这一观点。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家本色?
基辛格出色的外交行政生涯使其具有某种圆滑的性格特征。他在书中小心翼翼地,甚至是非常狡猾地避免对六位领导人某些有争议的政策进行评论。对戴高乐,他没有谈及法国撤离阿尔及利亚对非洲殖民体系在客观上的冲击;对尼克松,他没有谈及水门事件对美国政治体系带来的影响;对李光耀,他没有谈及极度实用主义的政策给小国决策带来的负面启示。
在基辛格的分析中,这些领导人固然是现实主义者,但理想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实用主义行动方式。这些领导者心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这一点基辛格毫不吝惜溢美之词,却在另一方面致力于淡化他们身上的马基雅维利色彩。这也让本书里的角色们多少变得人品高洁、行事磊落——戴高乐充其量只不过有些性格上的孤傲与不合群,而李光耀也无非只是说话风格直言不讳而已。而如我们所认知的那样,政治对人的塑造并非往往如此。
除了可以感受到基辛格一如既往地谨慎和圆滑,另外一层感受则是作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作者对六位政治家的观察视角具有丰富的层次,但并不总是准确。尽管与书中六位领导人均有较为近距离的接触,但时间和文化上的差距仍旧清晰可见。基辛格在描述尼克松的过程中明显叙事清晰,细节繁复。生于1876年的阿登纳与生于 1890年的戴高乐明显在年龄层次和历史认知上与基辛格差距较大,后者以仰望的角度观察两人,不免有隔靴搔痒的感觉。对于萨达特与李光耀,文化上的差异使作者更倾向于从性格和行为——而非战略思维上——理解两人,这无疑增加了认识这些人物的复杂程度。本质上,领导者也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人,只不过在决策中有时倾向于理性的选择,有时又倾向于本能的反应。作者在撰写《论领导力》之时,未免有将领导力的价值过度叙事之嫌。
但在整体上,基辛格通过仔细选择这六位领导者,突出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同质性领导力。以其广泛的国际交往经历来说,基辛格完全可以选择更多同时代领导人作为叙事对象。但这六人身上显而易见的同质性,能够最大程度地确保基辛格将他对领导力的认知和理解传递给更加久远的未来。如同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告别演说里反复强调“责任、荣誉和国家”以突出军人本色,基辛格也在自己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中,以启示录的方式,陈述了过去一百年里他所理解的政治家角色,那就是“勇气、毅力和战略”。他想告诉未来,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选自中信出版社《论领导力》一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