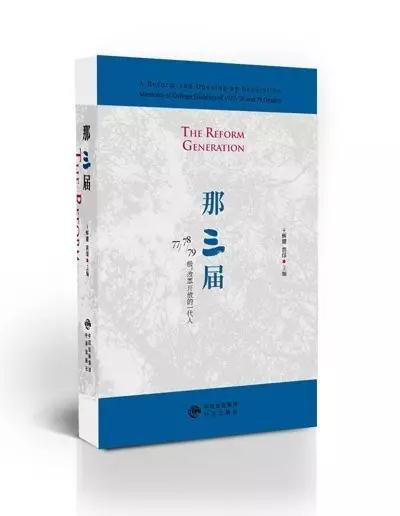刘宏:我的1978-回忆与思考
2017年6月28日
CCG图书:《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由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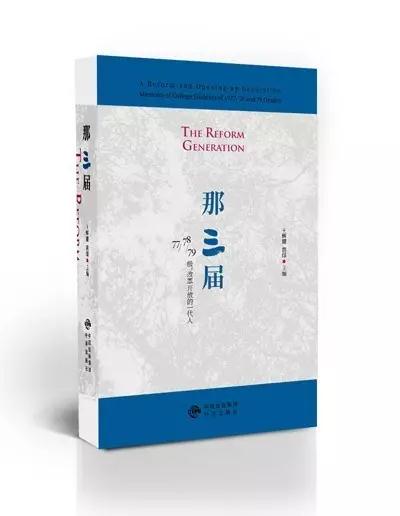
77、78、79 级,就是恢复高考后的连续三届经过不同寻常而又竞争异常激烈的考试而考上大学的大学生,他们是在十年浩劫中失去了高考机会的一代人,他们是以超低录取率从田间地头、工厂行业再入校门的一代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见证者、亲历者、推动者与捍卫者,他们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代人”。
刘宏,1978年10月就读于厦门大学历史系。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嘉庚讲席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主编、《华人研究国际学报》共同主编;《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助理院长、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系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及孔子学院院长。已出版中、英、印尼文专著12部及80多篇国际学术论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与亚洲国家关系、海外华人、国际人才战略与实践。

刘宏,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
作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1978年对我而言,不仅具有符号的意义,也是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和出发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
这个题目令自己颇感汗颜。无论是资历还是成就,自己都无法和本书中的同辈和同仁相比,更无颜在此王婆卖瓜。就权将“1978”、“回忆”、“思考”当作引子,带自己走回 35年前的厦门和那个时代,以及它们给我留下了哪些记忆、迷茫和憧憬。
现在参加高考的学生肯定无法想象1977年、1978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作为1978年恢复全国高考之后的首届高中毕业生,比起许多“老三届”和知青而言,自己的确非常幸运(其实,我跳级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虽然成绩超过了录取线,但因为“家庭成分”不过关,没被录取)。我当时就读的福建省永安三中,1978年共有八人考上全国重点大学(包括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等),这在那个小县城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出于对文科的兴趣和对厦门的喜爱(我在中学期间几乎每年暑期都会坐十个小时的慢车,到厦门的舅舅家去住几个星期,对阳光、沙滩和火车向往不已),我的第一志愿填报了厦门大学历史系,并被顺利录取。

刘宏的高考准考证
如果没有恢复高考的政策,包括我在内的一整代人的命运——以及中国的命运——将完全被改写。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高考考场墙外的大标语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1978 年初,国家的上山下乡政策还未取消,“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仍然是大多数高中毕业生不可摆脱的选择。家父当时还为我联系好了下乡的公社,为未录取作准备。
除了幸运的时代,当时老师的努力也为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生的高考升学提供了许多帮助。相比起今天的情况,那是个纯洁的时代,没有任何非教育和非学术的因素影响师生关系和学校教育。因此,当我们八个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食堂为老师们举行简陋的“谢师宴”时,我们送给永安三中的锦旗写的是 :“欣喜新苗出土逢甘霖、深感园丁辛勤育苗情”。
1978年10月,我踏上到厦门的列车,一出车站就被接到风景如画的厦门大学,住在芙蓉楼(二)308室(芙蓉楼是以厦大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先生的祖籍地命名的。也许是冥冥中注定,自己的未来生涯同陈、李二先生的文化遗产息息相关——不仅被任命为陈嘉庚讲席教授,还有幸在李先生曾任荣誉校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他作为创办人之一的南洋大学的校园内工作了十多年)。红绿交间的芙蓉楼当时面对的还是一片农田,远不如现在的芙蓉湖和嘉庚楼群美丽和壮观,但却有今天难以体念的清幽和宁静。记得一位室友曾写下他的感受,其中就有“倚绿红颜近,心随彩浪宽”的字句。而另一位同学在入学后不久登上鼓浪屿的日光岩后做诗,“更迎雄风上绝顶,遍吹心底自由花”。
每当看到同学们不同类型的才干,我都深感自己的不足并希望多向他们学习。我们7803班的57位同学,也可以说是当时社会的缩影。班上年龄最大的34岁,比我当时16岁的年龄高出一倍以上,他们绝大部分都有过上山下乡或工作的经历(我的同学包括今天中文传媒界的知名人物杨锦麟),无论学问修养还是社会阅历,都远远强于我们这些应届高中毕业生。那个特殊的时代,把我们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浓烈的学习氛围则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补回来”不仅仅是一个标语和口号,而是现实生活中的行动。
除了学习专业课和听取大量的学术讲座,我也被那个时代的文学所深深吸引。《人民文学》、《收获》和《小说月报》等文学刊物在我们文史哲图书馆经常是一刊难求,而刘心武、张贤亮、张承志等人更是大家讨论的话题。我们也有许多机会在全国高校中最大(能够容纳五千多人)的建南大礼堂观看《小花》、《庐山恋》、《望乡》、《追捕》、《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等。而最为难忘的或许是大家在私下传抄当时尚未公开出版的舒婷的诗。不仅因为她的朦胧,更因为她记载了那个承先启后的时代的迷茫和追求—— “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许多年之后,当笔者在厦门见到舒婷本人时,谈起那段经历,大家都不胜唏嘘。

大三郊游,左三为刘宏
1982年7月大学毕业时,在那个国家包分配和只有百分之五的适龄青年能上大学的年代,几乎每个同学都能顺利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自己则选择报考硕士研究生,在厦门大学修读现代东南亚历史。这不仅是因为厦大同南洋和华侨的不解渊源、它的师资力量,也因为家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归侨,同东南亚的联系还是很密切(虽然这种海外关系在“文革”期间是一种负资产)。三年的学习经历,我从厦大导师陈碧笙教授和黄焕宗教授处学到了做学问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也从复旦大学导师姚楠先生处了解到许多有关东南亚的第一手知识(由于制度的关系,厦门大学东南亚史专业1985年时尚无硕士授予权,笔者的硕士学位是复旦大学的,在复旦的答辩委员会主任是新加坡南洋学会的创办人姚楠先生)。除此之外,在厦门大学前后七年的求学经历为自己日后的学术追求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和学术人脉。(数年前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王赓武教授对着我们一群厦大毕业生说,今天中国国内外从事东南亚和海外华人问题研究的有许多都是厦门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
1985年7月硕士毕业后,当时北京有几个国家部委都愿意接受我去工作(那时国际问题的研究生可谓凤毛麟角),但是,最终我还是服从学校要求,留在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1987 年底,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厦门大学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并获得荷兰教育部资助,到厦门大学挑选进修生,当时正在研究印尼问题的我正好符合他们的选择要求,就第一次走出国门。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差距,到了荷兰后,我再次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不足:到阿姆斯特丹大学后,虽然荷兰语学了一点,但在研究中还是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由于自己研究的方向是东南亚,却对当地语言不了解,造成了研究印尼不会读印尼文的尴尬局面,而周围的同学不仅懂印尼文,还能用当地方言交流。
看到这种情况,我感觉到,只有掌握了语言工具,自己的研究才会更深入,才能进而了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框架。我1989年时得到了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五年全额博士奖学金,并开始全身心攻破语言关,但一个“偶然”机遇,使我改到美国读博士。当时,在美国研究东南亚的有八个全国性的研究中心,其中俄亥俄州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的印尼史教授Bill Frederick 恰巧就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访问,他和我谈了之后,表示可以支持我去俄大读博士。我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导师班国瑞(Gregor Benton)则作为我的美国签证申请的担保人,带我到大使馆面试,当场就顺利获得签证。
跟所有留美的学生一样,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对美国的人文和社会环境需要有个适应的过程,最大的心理适应是在学习上,我没想到在美国读博士用了将近六年的时间。不仅要上二十多门课和撰写大量的学术报告,还要通过四门课的资格考试后,才能开始做博士论文,在做博士论文前按规定还要通过除英语之外的另两种语言的考试(我用的是荷兰文和印尼文)。因为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国与印尼的关系,我在读博士期间花了一年时间到亚洲各地去做田野调查。1994年我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从事博士课题研究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的第一志愿还是回国工作),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研究系有意聘请我为讲师。我于1995年底获得博士学位后就任,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关系和海外华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在2000年被破格授予“终身教职”(tenure)。成为“终身教授”后,我本可在非常稳定的职业和日益上升的大学中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专业。可是,生活真的充满戏剧性,又一个挑战性的机会从天而降。这次的机会来自欧亚大陆的另一端。2004年,曼彻斯特大学和曼彻斯特理工大学合并后成了英国最大的大学。这个拥有36000多人的大学的新校长Alan Gilbert(原为墨尔本大学校长)计划开发六个全校性的新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研究”。这是由于近年来中国的崛起和在全球事务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校方觉得应该在大学里增加有关中国的教学和研究。我本人并不知道这个机会。与所有大学招聘资深管理人员和学者的程序一样,遴选委员会通过选择性的寻找候选人和海选的方式来招人。我是通过前一种方式,在经历了严格选拔后,并经由哈佛大学傅高义(Ezra Vogel)等知名教授的推荐,有幸在六十多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候选人中胜出。当时面试我的十人中包括大学的两个副校长、三个院长、工会负责人,另加两个校外的专家评委,这个庞大的阵仗我至今难以忘怀。而“雪上加霜”的是,我从波士顿到曼彻斯特的飞机行李没随人到,我临时借了一套西装出席面试。
虽然我知道了自己在众多竞争者中胜出的消息,但是,真的要离开新加坡去英国时,还是犹豫了:自己在新加坡工作十年了,虽然到了英国也是“终身教授”,但意味着要放弃在新加坡稳定的环境和良好的资源,到一个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国家一切要重新开始。在彷徨之际,我向我最敬佩的学者和前辈王赓武教授请教。他的一席话,使我决定辞去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终身教职,远赴英伦。当时人在美国的王教授告诉我,英国近年来大力发展中国和亚洲研究,而英国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发源地,曼大又是知名的国际级大学,我到了英国后定会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更有帮助,而且能够推动英国的中国研究。
除了教学和研究之外,近年来我还有幸在不同国家从事机构建制的工作(institution building)。在英国四年多期间(2006年6月至2010年9月),我担任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终身教授,并创建了校级的中国研究中心及孔子学院。前者是个实体机构,得到校方250万英镑的初期启动经费资助,有15个全职教师职位,提供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学位课程。孔子学院则是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由曼大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成立,宗旨是培养当地汉语教学的师资和介绍中国社会与文化。此后,作为中山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我推动成立了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侨务理论研究广东基地,并受委为学术委员会主任。
当我已经准备在英国进一步发展时,来自南洋的召唤又再次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2009年之后,南洋理工大学大力推动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在内的新学科建设,除了与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合办医学院之外,还要扩充2004年成立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大学希望我加盟,来共同推动和领导这一具有历史性的工作。2010年9月,我挥别了英伦,虽然没带走一片云彩,却也带走了四年多的西方工作经验和新的视野,包括在此期间建立的与中国相关部委的密切联系纽带(如外交部、国侨办、中组部、国家汉办)。
重返新加坡后,我先是担任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历史学暨亚洲研究陈嘉庚讲席教授,并从次年起就任这个拥有十个系和中心及三千多名学生的学院院长。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筹建历史学系,将自己的研究和教学重点定位于两个领域:全球史下的近现代亚洲、以科技、医学、环境和商业史为主的跨学科历史。在英国和新加坡机构建制的过程中,除了课程设计之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从全球招聘师资。过去五年来,我所评阅的工作申请不下500份,直接面试了近百名求职者。他们大多来自欧美,一部分则是出生于大陆、在海外受教育的学者(包括 77、 78 级)。今年,我们设立了中文驻校作家计划、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系,并计划明年成立哲学系和中英文翻译硕士课程。这样,我们的学科就能涵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虽然这些行政工作耗时耗力,但也使我有机会较为全面地和感性地了解当代中国研究、国际移民问题、亚洲史以及对外汉语教学等不同领域的最新进展情况,并有幸结识了该领域的一些佼佼者。
回首过去35年的经历,几乎是每换一个工作就换一个国家。我的思考和研究的轨迹也是在持续不断的跨界过程中完成的。过去六年来,自己先后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中国(中山大学)等国家和大学生活和工作了至少半年以上的时间。这期间还作为客座教授在哈佛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访学数月。这种跨越地理、文化、学术和政治疆界的经历对自己的研究至少带来三方面的影响:其一,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所代表的不同的人文和学术传统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其二,在与众多学者和学生的接触过程中,我不仅感受到多元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而且有机会直接而深入地了解“在地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关怀;其三,这几年的跨界研究历程使自己能够获得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无论是政府档案、口述历史访谈还是参与性观察。而这些历练对我的主要研究工作(当代中国、海外华人、国际人才战略与实践)来讲,尤具重要意义。我能取得些许成绩,和这些跨境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个不可复制的年代,1978年对我而言,不仅具有符号的意义,也是自己的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和出发点,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就我个人粗浅的认识来看,1978年有如下几个含义:
第一,时代比人强。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深知个人的作用是深刻地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如果我们那一代人不是生逢其时,获得高考这样一个最重要的平等的社会流动机会,个人无论再有才干也没有施展的空间和土壤。而在这种激荡的年代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织的环境下培育起来的毕业生,也有别于其他时期的学生,并能够对我们的时代和社会带来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第二,中国是世界的中国,国际是我们的舞台。1978年的另一层更深和更广的含义是改革与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也大规模地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成为全球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在文化和教育领域,全球化不仅体现在出国留学潮,而且也表现在中外思潮和观念的碰撞。我相信,我们那一代的人,没有人不知道《走向未来丛书》,没有人不受到各种各样新思潮的影响或感召。对我而言,1978年考入厦门大学,打开的不仅是进入知识殿堂的大门,而且也是与五彩缤纷世界接轨的起点。自己日后的跨国学习和工作经历能够较为顺利地展开,1978年功不可没。
第三,珍惜和把握机会,不断地充实自己。在1978年的大氛围之下,每个人都深知机会来之不易,因而都全力以赴地把握这种机会。对我而言,与比自己年长一倍的同学同窗四载,不仅成长更快,而且更多地感觉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以高标准来从严要求自己,成为前进道路上的一个动力。也许正是这种追求,使我能够在人生转折点上不致迷航太远。自己很幸运,能够从事自己喜欢又能够做好的事业。
第四,在回馈和服务社会的同时,我们更容易找到自己的坐标和价值。1979年底,清华大学77级学生提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并激励了当时中国所有的在校大学生和青年。77、78级是个充满社会责任感和积极入世的一代,为社会贡献的心态和行动伴随着我们不断成长。
的确,77和78级是不可复制的;不仅时代和环境已全然不同,作为那个时代产物的77、78级学生也是独特的。然而,那个时代和那一代人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和理念,应该是当代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为了同一个梦想和追求,它可以在新的环境下被复兴、改良和再造。这或许是我们纪念那个逝去的年代的终极目的吧。行文至此,我不由地想起了 1980 年传抄的舒婷的诗《一代人的呼声》:
……
但是,我站起来了
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
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
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
本文摘自《那三届——77、78、79级,改革开放的一代人》一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