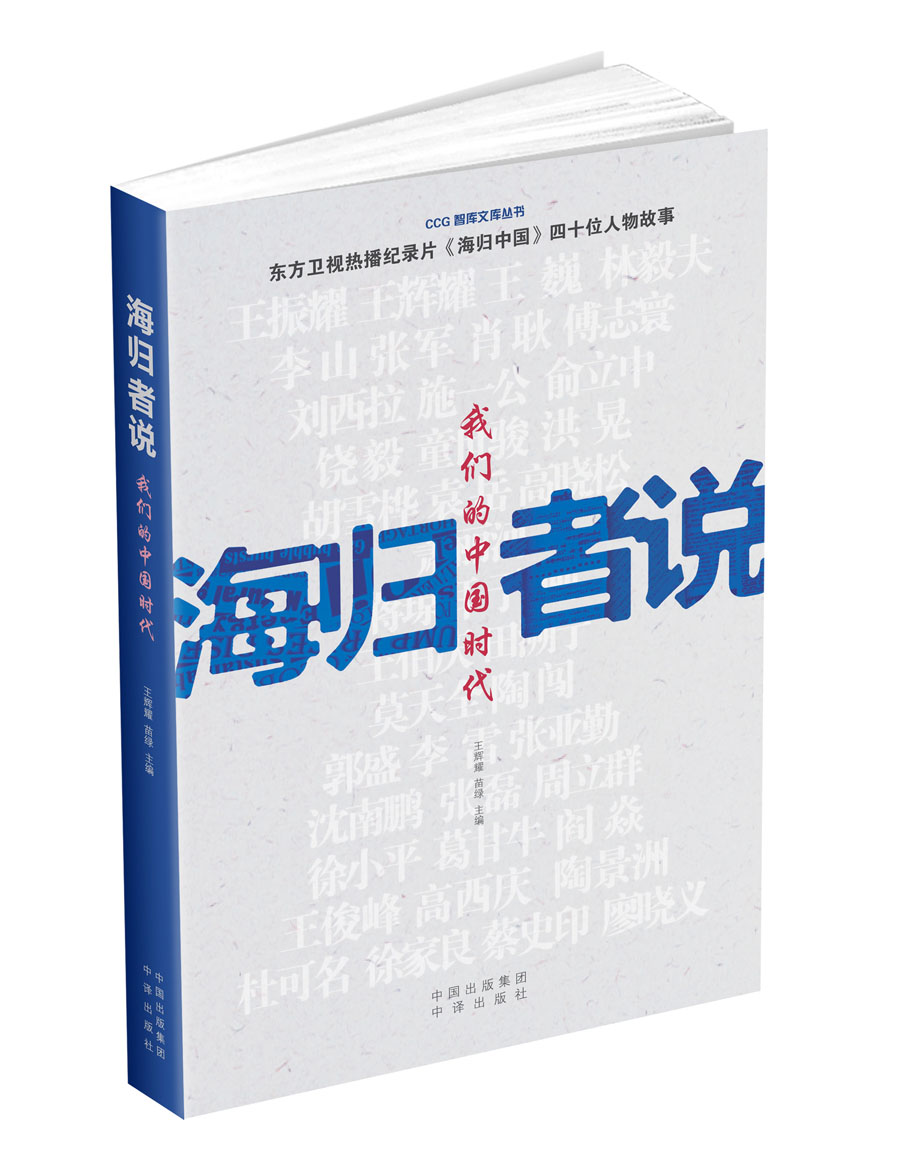饶毅:科学家的社会责任

▼
对我们这代人影响最大的事件是1977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在那以前,中国正规的高等教育停止了11年。我是78届,也是第一届应届高中毕业生考大学的,当时国家很重视科学,从科学教育出发推动国家进入新时代,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我的人生规划跟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背景都有关系。当时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高等教育,追求科学。我在大学四年以及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两年里,在科学上是有相当程度的准备的。我家里很多人都在大学或科研单位工作。所以,我去美国做的也是基础科学,虽然后来到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的医学院读研究生,但我对行医并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在科学方面打下更好的基础,以后做研究。
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绝大多数还是很关心中国的。1985到1991年,我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读研究生,但跟国内的导师、同事和一些科学家都有联系。中国科学院最早的《神经原》杂志还是我从美国这边的编辑部邮寄去的。后来,我到哈佛大学做博士后,之后又开始做助理教授。有一次在多伦多开会碰到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此后就跟中国科学院联系询问能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中国大规模的科研人员、自然科学人才流失,中国科学院很缺人。周光召先生很欢迎我们,就让当时负责生命科学的副院长许智宏、我和鲁白三个人在上海办一个联合实验室。
此外,我们后来还办一个国际会议,1998年开始在北京召开,2000年搬到了香港,现在是每两年开一次。1999年,我们跟蒲慕明成立了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后来德国科学家乌里?施瓦茨和我又共同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我担任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是因为当时科技部和北京市在新加坡一些华人学者的提议下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就又重新开始招聘,王晓东和邓兴旺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所长后就让我来做学术副所长。所以,我在任何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上都一直跟中国有联系。
实验科学要花很多时间读文献、做实验、写文章。在学生和博士后阶段实验都得自己做,但从助理教授开始,有实验室了,自己做实验的时间越来越少,多半是学生做实验。做实验少了,时间会空出一部分,而且我读文献很快,这样空出来的时间又多了一部分。我原来就喜欢看科学史,到美国以后希望搞清楚中国历史遗留的问题,开始看一些中国史,再看一些美国史。所以,我想有时间就写一点科普文章。
我在美国,在维护华人权益方面做过一些事情。在美国做研究的华裔,做学生的要比做教授的多得多,当然,你可以说这是语言的问题,但有时候并非语言的问题。我看过这类事情,一个招聘委员会,主任是个白人,一个中国人的申请过来,他连申请资料都没翻开就以语言不好为由拒绝了申请人。申请人写的材料可以显示他语言不好吗?如果只是一个中国名字就假定他语言不好,岂不是有问题吗?实际上,最后在美国做教授的人语言都相当好,但因为很多东西被白人挑过一遍,所以在学术刊物、学会和其他行政机构获得的荣誉等也会相对少一点。在美国,永远是你有机会就要讲出来,但华人不敢讲。我看到这个问题之后就写东西寄给各个学会、刊物。他们对这个很敏感,收到之后,有些刊物马上就改。
我不仅反对给华人设天花板,还反对过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美国神经科学会开年会是很大的学术会议,当时他们请达赖喇嘛来讲。我说这不对,这里面存在欺负人的问题。美国社会是具有相当宗教性质的社会,但美国科学家一般主张科学和宗教分开。虽然宗教很强大,但他们是不会请教皇过来在科学学术会议上演讲的。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请一个跟中国、亚洲有关的宗教代表人物过来,这里面有歧视。不能说在自己这边,科学家就是自由派,要跟宗教划清,到了别人那边就不管了。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反对达赖喇嘛到神经科学会演讲,这次反对对我影响很大。美国的科学家同行都认为我这是帮中国政府说话,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是2007年5月回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院长的,到2012年已经五年。当时学校认为我应该继续做下去,所以让我在院系领导的午餐会上讲一下过去五年的工作。我说不行,第一我得写下来,不能只说一下,要写一个材料,而且在吃饭的时候说太不正规了;第二我想不继续做了,在写的材料的最后一句就是我要辞掉院长的职务。
辞掉院长职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改革建立的体制里,对院长、教授、工作人员、学生都有相应的要求。理论上来说,应该由我的上级,也就是学校来规定院长怎么做。可中国的习惯是这样的,你搞改革,别人不对你这个职位的产生进行明确的规范,这也是很多改革最后改没了的原因之一。既然改革者要对自己的职位进行定义,那我要求自己肯定不做了,学校要通过像招聘我一样的模式,再招聘一个人。人选有了之后,给他的职权也要跟给我的一样,也就是说体制不是为我个人设计的,而是为这个职位设计的。后来,学校全部这样做了,院长产生和院长的职权也就制度化了,这样才算是做完了整个学院的体制改革。如果我这次不辞掉院长之职,那还要等我下次辞职的时候才能实现改革的制度化,这样改革就会被推迟。
在北京大学,我不仅在体制上进行了改革,也推动了文化上的改变。我一直希望招聘比自己好的人,所以我们大力引进了哈佛大学的谢晓亮教授。他是学化学的留学生中第一个做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把化学、物理的技术用于生物。引进之后,我们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全面支持,他成立的生物动态成像中心挂靠在生科院,有很多东西要我签字。我每次签字就像图章一样,问都不问。既然请人来做事情,就要全力支持。一定要在文化上有所改变,支持那些做得好的人,包括比自己做得好的人,而不能做成武大郎开店,别人不能比自己好,比自己好的人就不要。
文章选自《海归者说-我们的中国时代》,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苗绿、CCG主任王辉耀,中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