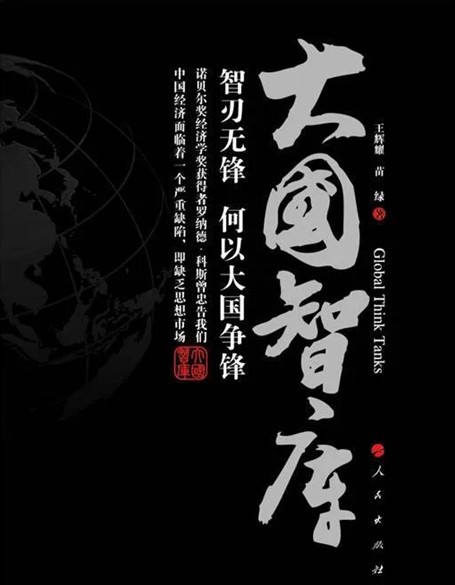【智库研究】美国智库的力量之源
智库的目的是影响政府决策,那么推动智库影响力发展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全球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肯教授给出的答案是:政治体制、公民社会、言论环境、经济发展程度、慈善文化、大学的数量和独立性等。 对此,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Antonie Van Agtmael将之更简洁的概括为:需求、人力与资金。他认为:“因为政治的去中心化和多元的政治文化使得智库有机会影响政策,很多学者希望通过自身对信息和知识的掌握帮助政府制定更好的政策,而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则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 而美国智库的幸运就在于,美国社会完全具备了詹姆斯.麦肯教授提到的要素,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1.独特的政治文化
所谓“政治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 任何政治体系或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它通过各种途径直接决定着每个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也影响着政治体系中每个政治角色的功能。 美国的政治文化表现为个人主义、实用主义和不信任政府,这为美国智库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个人主义的核心观念为,个人先于社会而存在,也就是说个人是本源,而社会是派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表现在政治方面就是有限政府,因为个人是本源,而政府存在的意义在于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所以,政府的权力需要受到限制。这些观点为智库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外在环境,为个人的建言献策与政府的从谏如流,奠定了思想基石。
实用主义强调实践对于社会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决定性意义。“有用即真理,真理即工具”的思想构建了美国人价值观念的基础,也俨然成为“美国精神”的代名词之一。正是由于这种“求实、求利、求效”的价值观念的盛行,美国智库才获得了存在并被认可的机会,并进一步发挥作用搭建起了沟通“知识”与“权力”的桥梁。
美国人对于政府与政客抱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感,因此格外重视通过制度设计避免私人空间受到政府权力的挤压以及官员腐败现象的产生。美国民众的这种心态,使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五种权力”——智库更容易获得一般民众的信任,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满足了美国公众监督政府的需要。当然,这也使民众也对智库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待。
2.开放的政治体制
欧美国家政治体制的特色在于三权分立(三权分治),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的竞争,使得总统和国会需要大量的参谋人员,以便在决策中获得优势地位。正如学者所说:“尽管看起来国会和行政部门内不断增多的专业人员及在政府内建立政策研究机构将会减少对智库的需求,但事实恰好相反。”
美国属于两党制国家,两大势均力敌的政党——共和党与民主党,通过总统与议会竞选轮流执政。两党议员以及总统候选人为赢得竞选,需要研究机构来充当智囊,但两党都没有自己正式的政策研究机构(附属于民主党领导人委员会的进步政策研究所是唯一的例外) ,这就促使他们就会向智库政策专家咨询,听取他们的专业意见。而且总统组阁时一般都会考虑各个智库政策专家的意见,特别是在过渡时期,总统施政对智库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3.雄厚的资金支撑
中国有句古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离开资金的支持智库的生存都受到威胁,更不用谈发展了。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影响美国智库媒介曝光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资金,美国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智库运营资金都不少于1000万美元。” 雄厚的资金支撑是美国智库维系正常运转与扩大影响力的物质基础。
大多数美国智库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基金会、企业、个人捐款和政府合同。其中,基金会是一种相对稳定和长期的资金来源。据2000年版美国《基金会年鉴》提供的数据,2000年资产在300万美元以上,年捐款在20万美元以上的基金会共有10492家,而这还不到当时美国基金会总数的1/4。这些基金会控制着多达3000亿美元的资产。 20世纪80年代,基金会对政策研究机构的大规模资助,促成了当时美国智库数量激增局面的出现。1982~1987年间,美国基金会对智库的资助总额从5.2%上升到10%,具体而言就是从70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
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也是智库的资金来源之一。以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为例,2007年度,在其将近3000万美元的运营资金中,39%来自于企业,10%来自于个人捐赠。 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不仅为智库的正常运营提供了物质支撑,也有利于智库保持和坚守其独立性。
4.完善的法律法规
美国的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为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而美国慈善传统和基金会文化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其完善的法律法规。美国的法律法规对形成这种环境起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相关免税待遇。
美国税法501(c)3规定,符合下述三个条件的组织可以享受免税待遇:一是该组织的运作完全是为了从事慈善性、教育性、宗教性和科学性的事业,或者是为了达到该税法明文规定的其他目的;二是该组织的净收入不能用于使私人受惠;三是该组织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不是为了影响立法,也不干预公开选举。 因此,在美国,智库在注册为非营利的免税组织后,只需要再成立一个以宣传各种政策为内容的教育组织,就可以取得非营利机构的法定资格,并在税收制度上获得免税的优惠待遇。
其二,慈善捐款制度。
美国慈善税法通过捐助慈善,减免税收的方式,鼓励美国富豪们创立基金会。此外,高额的遗产税也是美国富人倾向于将财产捐赠给社会的重要因素。
5.便利的“旋转门”机制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独有的特色,它实现了智库研究人员和从政人员的自由和双向流动,进进出出的流动有利于提升智库的社会影响力。
早在20世纪初期,美国的“旋转门”机制就发展成熟了。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是美国第一位从学界进入政界的总统,在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他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校长。目前,在奥巴马的执政团队中,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就曾经多次通过“旋转门”实现身份的转换。詹姆斯.斯坦伯格曾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和兰德公司研究多年,之后成为克林顿政府外交团队的重要一员。克林顿政府任期届满后,他又进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效力于奥巴马政府。
要说旋转门机制最明显的,首推里根政府时期。在里根的8年任期里,他共聘请近200名智库成员到政府任职或担任政府顾问。这近200名人员中,55名来自胡佛研究所,36名来自传统基金会,34名来自企业研究所,32名来自当前危机研究委员会,18名来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
2009年,奥巴马入驻白宫之后,邀请了32名布鲁金斯学会的成员进入其执政团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担任驻联合国大使的苏珊.赖斯(Susan Rice)、担任白宫国安会亚太资深主任的贝德(Jeff Bader)、担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萨默斯(Larry Summers)以及担任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Jim Steinberg)等。
对于总统邀请智库人员进入其执政团队的原因,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可以给出一个答案。他说“我也许不能告诉你东帝汶的情况,但我会请那些有经验的人,比如赖斯(胡佛研究所)、沃尔福威茨(1994年开始担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学院院长)、切尼。我的高明之处在于我知道自己哪些不懂,但却有极好的判断力,判断哪些信息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
旋转门机制,为美国智库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影响国家、政府决策的最便捷通道。智库研究人员长期专注某一领域的研究一旦成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思想、经济等方面的理念便容易得到贯彻实施。而政要加入智库,则增加了智库与政府的联系,为智库产出更多被政府采纳、影响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6.多元的政府沟通机制
在美国,智库和政府的交流方式众多,智库通过派人参加政府的听证会和国会举行的各种活动来及时了解政府政策的变化和走向。同时,智库还举办各种培训会,对政府人员进行培训,或邀请政府人员与智库成员一起做课题、搞研究,让政府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成果。这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同时也提高了智库自身的影响力,提升了政府人员的理论水平。
美国知名智库,如传统基金会、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外交关系委员会、兰德公司、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等,都有类似活动和交流项目。如,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和布鲁金斯举办的“加迪斯—开普”中东问题论坛就邀请了美国政府官员参加,有力地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亚太地区高级学者研讨班,每年专门从美国国务院、国防部等部门招聘人员一同开展研究。通过共同研究,学者既了解到了美国现行的各项政策、主张,也把自己的思想理念传递给了政府,从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